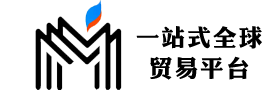“现在我们面临的危机,如果分析底层原因,跟世界的‘极化’(Polariza tion)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关。以美国为例,1978~2015年,收入处于后50%的人群的收入扣除物价之后几乎没有增长,处于中间40%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扣除物价之后的平均年增速仅为0.9%。”
6月28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新发展阶段包容性增长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题为《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政策选择》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并没有在增长中受益,形成了一个极化的、针锋相对的对立,这是当前很多问题以及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底层根源。
解决城乡差距,首先要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刘俏表示,我国经济在过去40年高歌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假说认为,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着人均GDP增长,基尼系数先上升,然后逐渐下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数据呈现“正U形”,基尼系数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人均GDP提升而下降,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水平比较高的阶段,这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未来讨论高质量增长、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对此应加以关注和考虑。
刘俏指出,我国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上。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6倍,在西部地区达到了2.66倍。大量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非常低,财产性收入占比更低。“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要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刘俏称,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均衡发展所需要思考的最大问题。
谈及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底层原因,刘俏分析称,一方面,整个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整个农村转移人口、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也相对比较低。
202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比高达24%,却只贡献了7.7%的GDP。刘俏预测,到2035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农业在GDP中的占比或下降至3%左右,而就业人口则下降到6%。这意味着将有18%的人口需要跨行业转移,以当前7.5亿就业人口计算,未来十几年里,有1.35亿农业就业人口需要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转移。
对于如何缩小农业、农村就业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口的差距,刘俏认为,首先要通过乡村振兴增加对农业、农村、农业人口的投入,大力提升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全面推进农业工业化。同时,让农村用地能够真正流转,提升农村人口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研究显示,在过去40多年里,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刘俏表示,如果要提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此作为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方法,就需要对“三农”进行大量的投资,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投资率。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和程度
刘俏指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和长租公寓等建设,真正推行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和程度。
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非常低,他们的有效工作时间、收入来源、发展机会跟城市居民不一样,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也不对等,这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推进“橄榄型社会”形成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刘俏表示,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测算人口适合度指数,尽管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城市分布情况仍不合理。光华思想力课题组在研究中有一个重要发现:69%的城市人口规模适合度小于0.5,87%的城市实际人口规模小于最优规模,也有超10%的城市人口规模比理想规模偏大。如果城市人口不足,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新兴产业很难涌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可能变成无效投资。
“让农民工、城市灵活就业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真正变成新市民,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一个可行的政策路径。”刘俏称,未来一定要让更多的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化,真正让城市的人口分布变得更加适宜。
谈及具体的政策,刘俏表示,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当前,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不缴纳公积金,享受不到对等的公共服务,需要把他们纳入到这个体系里。另外,全国范围内公积金每年大概有8000亿~1万亿元的资金结存,可由公积金中心来引导,大规模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或长租公寓,针对不同的新市民群体给予不同层级的供给,让每年超过1300多万的新市民能够在城市住下来,而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其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都将会得以提升。
而从新市民角度看,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住下来,他们的消费能力、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有所提升,对于解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这是很重要的解决途径。
宏观政策还有巨大空间,财政政策可更积极
刘俏还提出,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在解决共同富裕、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当前财政政策还有巨大的实施空间,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他指出,财政政策的空间来源于发行公共债务,只要公共债务的利率小于GDP增长速度,基本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具有可持续性。
刘俏指出,世界各国政府都对提升公共债务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特别担心国家债务快速增长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所以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去解决急需解决的节点问题、关键问题时,总会有所顾虑。
对此,刘俏认为,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行转移支付、实现共同富裕时,变得比较谨慎,这或会带来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
刘俏表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远大于GDP,拥有实施宏观政策的巨大空间。分析过去30年全球爆发的所有金融危机,发现金德尔伯格、明斯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实证证据支持——一个经济体在过去三年经历债务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大幅提升,未来三年内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是45%。然而,这一结论对于那些政策空间较大的国家(整体价值远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样情况下,这些危机爆发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换言之,即使我国在过去三年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不高,只有7%左右,远低于平均值45%,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
刘俏认为,通过举债或者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资金是配置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节点上,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金,会带来经济社会正向良性的发展,而且对危机的爆发是有遏制作用的。
刘俏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实施积极宏观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在这个背景下,未来在追求包容性增长、在政策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时候,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一些。比如,可以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甚至发放现金,或许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长远讲,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低收入群体、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进行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刘俏认为,这对于从中长期维度来推进包容性增长,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想,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作为未来的政策选项,可以更加积极地服务于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这样的目标。”刘俏表示。